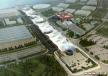解读国资“新家法”
2010-08-26 15:25:32 来源:新闻周刊
作为国资法正式出台前的过渡,《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被人们寄予了厚望,这些愿望会否落空还要看国资该改革能够沿着条例走多远
“可以这样说,我们公布的这个暂行条例是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以及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首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如是评价《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简称《条例》)。
在国资改革这条新长征路上,如果用“百步者半九十”来形容国资委的建立,那么剩下的一半就取决于即将实施的《条例》,以及目前尚待字闺中的《国资法》了,它们最终将给出答案——关于174000亿国有资产的未来命运。
事实上,这前面的九十步已经是一次旷日持久的跋涉。当国资委开始以一个超级“特设机构”亮相于今春的时候,人们开始猜测这个手握数万亿资产的“国资老板”将会实施怎样的新政。
“变局乍现,对于历经了10年探索的国资管理体制变革历程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各路媒体纷纷以欢呼的姿态迎接这个机构的诞生。
3个月后的现在,欢呼隐去,一切开始真正浮出水面。
《条例》暂“代”法
名里有乾坤,在原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李保民看来,此次《条例》的名称中就藏有玄机,“用的是‘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而没像过去常用的‘国有企业’和‘国营企业’。”在此之前的有关条例如1994年7月24日国务院发布的《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以及2000年3月15日国务院签发的《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都还是“国有企业”冠名。
事实上,“企业国有资产”是一个内涵极其深广的新概念,这其中蕴藏着变化的玄机是中国从“国营企业”到“国有企业”再到“国资企业”的历史性变迁。现在“我们不再关注他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我们关心的是企业有没有国有资产,这些资产效益如何?”李保民说。
当人们回头重读十六大报告的时候,也许会发现:有关国资改革的标题中竟没有提到“国有企业”这个词,在谈到国资改革的时候,“国企”概念已经悄然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国有经济的载体——“国有资本”。
“国资委和企业是一个大家庭,我们监管6.9万亿的资产,打个比喻,就相当于6.9万亿的大董事会。”国资委副主任李毅中在这个大家庭的“新家法”——《条例》即将付诸实施的时候告诉中外记者他所理解的国资委是什么。
这样一个大家庭,没有规矩怎成方圆?全新定位下的国资委显然要进行开创性的工作,但是“规矩”的问题似乎被“惊艳”于国资委机构本身的人们忽略了,这些规矩包括许多方面:譬如,国资委如何“管”企业?国资委如何实现“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对国资委应该有什么样的约束机制?需要不需要“三个层次”?国有股转让如何定价以及如何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等等。
“我想,对于这些问题,暂行条例给出了一些答案,但并不是全部,有些问题需要在以后的具体细则中做明确规定,而有些问题可能需要等以后的国资管理法才能给出答案。”参与《条例》草案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的国资体制改革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研究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台《条例》的意义在于:“用行政法规的办法来弥补法律的不足和缺失,《条例》就相当于现阶段的《国资法》。”同样参与《条例》修改的李保民说。
《国资法》的出台时间,鉴于程序上的复杂性以及国资改革的曲折性尚需较长时日,“至少今年难以出台”。
“准分级所有制”
从地方刮风式的出售国企到中央紧急刹车,这种来回折腾的情形几乎成为10年来中国地方国资改革难以逃脱的宿命。现在,就在国资委成立之初,类似的情形似乎开始复燃,关于地方国资管理机构要赶在地方国资委成立之前享受“最后的盛宴”的说法不胫而走。人们担心,国有资产流失的新一轮高潮就在眼前。
“实际上,这是一个长期以来的误区,—提到出售国有资产就认为是资产流失。”张文魁说。他最担心的是:“国有资产尽管可以避免在出售的过程中流失但会在不流动的过程中完全消失”,实际上这种中央和地方的“拉锯战”最终会导致“国资改革丧失时机”。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形的一再上演呢?事实上国资委的成立恰恰就是直指这个问题的核心——中央和地方难以分级享有产权。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架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样,国资改革的操作中心将由中央挪到地方。
这被学者们称为“准分级所有制”。就在3个月前人们普遍担心的是,新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首要任务——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合理和公平地划分资产,世界银行国企问题专家张春霖就曾直言:“光这些事就够新国资机构忙上一年了。”但是现在看来,这些已不是问题,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一共是196家,国有资产总量是6.9万亿人民币”。
然而,一个隐忧似乎已经埋下伏笔,“《条例》只是简单地规定国务院国资委对地方政府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有‘指导和监督’的职能。但到底指导监督什么,如何指导监督,并没有清楚的规定,这样,就可能导致国务院国资委侵蚀地方政府和地方国资委对所属国资的合理的出资人权利,可能会利用‘指导和监督’的权力干预地方的国企改革和国有股转让等事务。”张文魁说。
有理由担心,只要国务院国资委念起“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这样一个紧箍咒,地方就无法积极推动国企改革和国有股转让等工作。
关于这个问题,专家认为,最核心的需要落实“准分级所有”精神,明确国务院国资委与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之间的职责范围和权利。因为这涉及到新的国资管理体制能否有力地推动国企改革和国有股转让,涉及到如何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等等。
“新国资管理体制的灵魂就是‘准分级所有’,不在这个方面下工夫,而过度关注其他一些枝节性的问题,反而会本末倒置。”张文魁说。他认为,为了落实“准分级所有”的精神,中央对地方政府行使产权的资产只应保留四项权利,第一,由中央统一确定须由国有资本控制的领域,第二,由中央统一确定国有股转让须符合公开性竞争性的程序,以保证不发生大规模的国资流失,第三,由中央统一确定国有股转让收入的使用办法以保证职工分流和社保,以及国企显性和隐性债务能得到优先解决,第四,由中央统一确定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的内容和格式。国务院国资委对地方政府国资管理的“指导与监督”也仅仅体现在这四个方面。
这样,只要中央有这四项权利而且只有这四项权利,地方就可以大胆地推动国企改革和国有股转让,而且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国有资产流失。
三层模式要不要坚持?
国资委→中间层公司→一般生产经营企业,这种国资三层管理模式目前已经在全国流行甚广,因为它可以避免“政企界面不清”和解决国有企业过多、直接管理幅度过大的问题。
但是,“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条例》并无具体规定,在未来的实际工作中是无法回避的。”张文魁说。
他的调研表明,中间层公司利弊兼有。其积极作用主要是,对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问题有积极作用;中间层公司通过必要的监管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第三层的生产经营企业乱投资、乱担保乃至企业“内部人控制”和财产非法转移有积极作用;中间层公司在多数情况下对第三层生产经营企业同时行使“管资产”与“管人”的权力,即可以选择、任免第三层生产经营企业的领导人,能够促进经理人市场化,按照市场方式建立激励制度;第四,对持股的国有企业之间的资产重组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等。
但作为一把双刃剑,中间层公司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一些中间层公司不满足于仅承担股权和资产管理的角色,还积极开发实业,有些业务与其控股的公司有潜在甚至明显的利益冲突;一些企业认为中间层公司对投资、担保等的审批不利于企业自主经营,限制了企业的发展;中间层公司的一些资产重组安排存在“抽肥补瘦”的问题;中间层公司按政府要求安排了许多活动,被认为是增加企业负担的政府“二传手”等。
张文魁认为,在未来的实际工作中,“两层次”和“三层次”可以并存。“三层次”不是惟一的模式,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可以由“统一权责”的所有权行使机构直接进行所有权管理。对于有必要设立的中间层公司,国资委应该将其界定为特殊公司,并参照国外的特殊法人制度,由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其职能、运作规则、决策制度、财务制度、治理结构等作特殊安排。“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作这样的特殊安排的可能性是较大的。”张说。
“弱势”国资委会否强权?
“与十六大报告中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国资委设想相比,现在我们看到的国资委已经算是‘弱势’登台了。”中国社科院钟伟持有的这种观点实属另类。
事实上,如果前后比较便知此言不虚。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仅196家企业;其中有约50家的大型工业企业的人事任免权并未归入国资委;而国有资产中金融性质的资产也交由银监会和保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接管;“人们担心他过于强权,反而导致了它的弱势登台。”钟伟说。同样,李保民的课题组在年初的时候甚至建议由一位副总理来兼任国资委的主任,但并未采纳。
即便如此,人们仍然普遍担心国资委会变成“老板”加“婆婆”的强权机构,“老板”自然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是“婆婆”就回到了过去的老路上。“我们这个机构从国务院的授权上就没有授给我‘婆婆’的权。”李荣融说。
“尽管《条例》明确指出,国资委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条例的规定是一回事,实际当中可能又会是另一回事。”张文魁担心,在实际工作中,防止国资委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将不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原因何在?国资委对企业负责人的管理真正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来运行尚需时日。《公司法》规定,包括大股东在内的任何股东,可以通过股东会来行使规定的权利,包括董事的选举权、资本结构变化的投票权等等,但中国的国有大股东往往把大股东在股东会上的主导权,理解成日常决定权,从而导致权利的严重滥用,不但会干预董事会、经理的权力,也会侵害小股东的利益。
老板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权力。国资委是东家,在国有独资公司中是惟一股东,在国有控股公司中是大股东,“更有可能不顾公司法等法律规定的程序,在企业投资决策等方面进行不正当的干预。尤其是,国资委如果直截了当地任免企业负责人的,通过‘管乌纱帽’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影响企业的决策。”李保民说。
众所周知,要防止国资委滥用权力就必须应该有约束机制。“《条例》专门谈到了各方的法律责任,包括国资委不尽职或者滥用权力的法律责任,但这些法律责任大部分属于行政处分,且不易轻易界定,所以并不会有太大的实际应用价值。”张文魁说。他认为,应该建立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同级国资委的问责制度,特别是每级政府都应该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该预算由同级人大审议和通过。资本经营预算及其与一般公共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之间的资金转移关系由同级人大决定。
但是,钟伟担心这种问责会否有效,“问是好问,责何以责?通过人事是不可能的,这种问责缺乏真正可以约束的手段。”事实上,来自人大的监督尤其是体现在重大国有资产的处置权上是国有资产在产权关系上的必然要求,但是目前关于人大、国资委以及国有资产投资机构各自的权限如何划分,仍是新国资管理体制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现在,我们只是探索着又往前走了一步。”李保民说。一切还要看国资改革能够沿着《条例》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