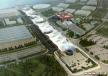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吕梁为什么另案处理
2010-08-26 15:11:19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号称“中国股市第一案”的中科创业案选择在四月的第一天在北京宣判,结果出人意料,最高的才判处有期徒刑4年。自首的索性就免于刑事处罚。据在现场采访的北京电视台记者描述,当事人在听到宣判后居然笑了起来,而旁听者却一片哗然。
“特别关注”的栏目记者问水皮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水皮的回答是,基本正常。
为什么影响这么大的案例会作出这样的判决呢?
原因一是这种案例按律最高是5年有期徒刑。
原因二是中科创业案的主犯们都没有出现在被告席上,现在的当事人并非主谋,按首犯必惩,胁从从宽的原则,判成这样已经算不错了。
当然,犯罪嫌疑人在听到判决后的表情是极不严肃的,但话讲回来你要他装着痛心疾首的样子也不可能,因为从案发到今天已经整整三年,判四年刑的也就实际只有一年的牢可坐,其他不满三年的或可当庭释放,他们能不为此而轻松,能不为此而高兴,能不为此而发笑?这种笑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笑,你挡都挡不住的。
那么,大家的损失怎么办?
打开中科创业,也就是现在ST康达尔的K线图我们可以发现,现在仅值5元钱的股票最高峰位曾经到达过80元左右。在2000年12月25日第一个跌停板出现的时候,康达尔的股价一直维持在35元左右,连续9个跌停板之后,康达尔就只剩下10多元钱。从康达尔的K线图上就可以看出一个清楚的轨迹,康达尔变成中科创业的过程是一个股价急剧飙升的过程;1998年当控盘康达尔这个“养鸡专业户”被深深套牢的深圳大户朱焕良北上寻求吕梁“解套”良方的时候,康达尔的股价只有8块左右;而当1999年,也就是一年后,吕梁组织“北京机构”成立“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时候,康达尔的股价,确切的说当时已经改名叫“中科创业”的股价已经牢牢地站住了40多元的高位;2000年则是康达尔经历在“欢乐中死亡”的终极体验,由于互联网泡沫,由于中科创业的名头,由于公司“金融+高科技”的概念,康达尔从40元上冲84元的过程并非完全由庄家操纵完成,而是“股票自己涨,压都压不住”。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吕梁自己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战略投资”梦幻中,其他的利益中人包括当初找他的“朱大户”朱焕良为什么不见好就收,逢高出货呢?对于吕梁而言如果还有被“假到真时真亦假”所迷惑的因素,那么对于普通的投资者而言难道他们真的幼稚到以为深圳的一个养鸡场会生出“金蛋”来吗?
大家的损失现在看来也就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了,根据高院的司法解释,股民索赔也就局限在因为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而造成的投资损失。而在吕梁一案中,尽管董事会曾经被来自吕梁和朱焕良的手下把持,但是公司本身是无辜的,退一万步讲,即使能认定康达尔有虚假陈述的事实,康达尔能作为民事赔偿的被告也没有实际意义,康达尔现在已经被ST了,等待他的命运很可能就是退市,破产,告与不告的结果是一样的。至于说吕梁现在则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大家就是想告都找不到这个人,更没有实际意义。
当然,中科创业案的意义并不在于投资者的损失,中科创业案的意义恰恰在于案由的特殊性。如果不是这种特殊性,北京二中院也不会超限审判时间长达10个月,如果不是这种特殊性,北京二中院也就不必再向北京高院请示汇报,如果前期有案例可循,那么中科创业案也就不会引起媒体的强烈关注,而特殊之中的特殊还在于这是一起主犯没有到庭的审判,这个主犯策划、操作了所有的过程,甚至直接发出了“中科系雪崩内幕”的新闻稿并且相当长一段时间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触犯法律,只是感到事态失控才直接“跳”出来,如果吕梁在押,也许中科创业案会是另外一幕情景,也许只是巧合,四月的第一天就是“愚人节”。
“特别关注”的栏目记者问水皮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水皮的回答是,基本正常。
为什么影响这么大的案例会作出这样的判决呢?
原因一是这种案例按律最高是5年有期徒刑。
原因二是中科创业案的主犯们都没有出现在被告席上,现在的当事人并非主谋,按首犯必惩,胁从从宽的原则,判成这样已经算不错了。
当然,犯罪嫌疑人在听到判决后的表情是极不严肃的,但话讲回来你要他装着痛心疾首的样子也不可能,因为从案发到今天已经整整三年,判四年刑的也就实际只有一年的牢可坐,其他不满三年的或可当庭释放,他们能不为此而轻松,能不为此而高兴,能不为此而发笑?这种笑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笑,你挡都挡不住的。
那么,大家的损失怎么办?
打开中科创业,也就是现在ST康达尔的K线图我们可以发现,现在仅值5元钱的股票最高峰位曾经到达过80元左右。在2000年12月25日第一个跌停板出现的时候,康达尔的股价一直维持在35元左右,连续9个跌停板之后,康达尔就只剩下10多元钱。从康达尔的K线图上就可以看出一个清楚的轨迹,康达尔变成中科创业的过程是一个股价急剧飙升的过程;1998年当控盘康达尔这个“养鸡专业户”被深深套牢的深圳大户朱焕良北上寻求吕梁“解套”良方的时候,康达尔的股价只有8块左右;而当1999年,也就是一年后,吕梁组织“北京机构”成立“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时候,康达尔的股价,确切的说当时已经改名叫“中科创业”的股价已经牢牢地站住了40多元的高位;2000年则是康达尔经历在“欢乐中死亡”的终极体验,由于互联网泡沫,由于中科创业的名头,由于公司“金融+高科技”的概念,康达尔从40元上冲84元的过程并非完全由庄家操纵完成,而是“股票自己涨,压都压不住”。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吕梁自己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战略投资”梦幻中,其他的利益中人包括当初找他的“朱大户”朱焕良为什么不见好就收,逢高出货呢?对于吕梁而言如果还有被“假到真时真亦假”所迷惑的因素,那么对于普通的投资者而言难道他们真的幼稚到以为深圳的一个养鸡场会生出“金蛋”来吗?
大家的损失现在看来也就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了,根据高院的司法解释,股民索赔也就局限在因为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而造成的投资损失。而在吕梁一案中,尽管董事会曾经被来自吕梁和朱焕良的手下把持,但是公司本身是无辜的,退一万步讲,即使能认定康达尔有虚假陈述的事实,康达尔能作为民事赔偿的被告也没有实际意义,康达尔现在已经被ST了,等待他的命运很可能就是退市,破产,告与不告的结果是一样的。至于说吕梁现在则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大家就是想告都找不到这个人,更没有实际意义。
当然,中科创业案的意义并不在于投资者的损失,中科创业案的意义恰恰在于案由的特殊性。如果不是这种特殊性,北京二中院也不会超限审判时间长达10个月,如果不是这种特殊性,北京二中院也就不必再向北京高院请示汇报,如果前期有案例可循,那么中科创业案也就不会引起媒体的强烈关注,而特殊之中的特殊还在于这是一起主犯没有到庭的审判,这个主犯策划、操作了所有的过程,甚至直接发出了“中科系雪崩内幕”的新闻稿并且相当长一段时间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触犯法律,只是感到事态失控才直接“跳”出来,如果吕梁在押,也许中科创业案会是另外一幕情景,也许只是巧合,四月的第一天就是“愚人节”。